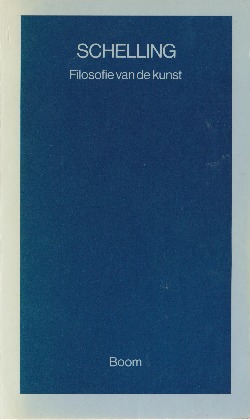约斯·德·穆尔 著《阐释学视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麦永雄 方頠玮 译 《外国美学》第20辑 [Jos de Mul,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no. 20 (2012), 312-336]
阐释学视
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1]约斯·德·穆尔 著 麦永雄 方頠玮 译
摘要:本文从 “经验视界”的常用隐喻出发,探讨文化间性阐释学(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的三种不同类型,它分别把阐释学的诠释构想成视界拓展,视界融合和视界播撒。可以认为,阐释学史上这些赓续的阶段分别源于——但并非是严格地限于——全球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以中西语言和哲学相遇合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契机为例,对文化间性阐释学这三种类型的优长和不足展开讨论。要论辩的是,尽管从理论的视野来看,这三种阐释学类型是互相排斥的,但是作为当代阐释的存在方式,我们有赖于这三种不同的阐释学实践,并且无法避免地与它们共生。
关键词:文化间性阐释学;全球化;阐释学视界;汉语;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柏拉图;孔子;徐冰
给我视界。
——杰克·斯帕罗船长
一. 导论
全球化作为人口、观念、习惯和商品的全球循环交流,并不是一种近期的新现象。大约在两百万年前,我们的的始祖直立人带着他们的习俗和石器时代的工具走出非洲,散布到其他大陆,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观点:全球化是人类自起源时就具备的特性。况且,当我们纵观我们这个智人物种的历史时,会发现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速的历史。早在公元前三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之间就有重要的贸易联系。几千年之后,丝绸之路开始连接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国汉朝的经济与文化。然而,正如全球化KOF(各国经济发展指标)指数所表明的,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由于新的交通和电讯方式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每一位世界公民生活中的决定性现象,从世界金融资本业的银行家到发展中国家的糖果店小职员都受到影响[2]。
全球化从根本上对人类生活和文化的每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对经济和自然环境深具意义,也影响了社会关系、政治、宗教、娱乐和语言,这里仅列举少数受到影响的领域。这些影响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范围从优势基因、知识、技术和文化宝藏的全球分布,到开发、文化同化、战争、传染病的传播和生态灾难。
全球化也是一种阐释学挑战。在不同文化的际遇中,人员、观念、习俗和商品在的交流常常是陌生的,需要通过解释才能获得理解。在本文中,我将分析文化间性阐释学的挑战与陷阱。从(个人与文化的)“经验视界”的常用隐喻出发 ,拟讨论文化间性阐释学的三种不同类型,它们分别被构想为阐释学诠释的视界拓展,视界融合和视界播撒。我将要讨论的是阐释学史上这些赓续的阶段分别源于——但并非是严格地限于——全球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通过列举中西语言和哲学在跨文化境遇里碰撞的一些典型实例,我认为这三类阐释学各有其特定的利弊。我将要深入的讨论,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三种阐释学类型是互相排斥的,但是作为当代阐释的存在方式,我们有赖于这三种不同的阐释学实践,并且无法避免地与它们共生。
二. 人类经验的视界(The horizon of human experience)
在阐释学史上,“视界”这个词语常常被用来形容人类经验的基本限度。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人类自身与人类文化都是有限度的。受限于时间,是因为他们具有开始和结束的特征。而受限于空间,是因为他们只能在广袤的宇宙空间里栖居于一小块地方。鉴于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度,人类经验必然是有限的。我们总是生存在一种特定的视界里——空间与时间,个人与文化,文学与隐喻的视界。在这种视界中,许多经验和表达方式都是熟悉的,无需(多加)解释就能轻易地得到理解。但另外有一些表达方式却远离了我们经验视界的中心。在这种受到时间和空间距离限制的情况下,我们体验的是陌生的和奇怪的情况,往往会疑虑丛生。譬如,当我们遇到了数百年前书写的文本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些文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视界或迥异于我们文化的思想、习惯和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体验到不解和误解,我们感到解释与沟通的需要。实际上,阐释学的实践与反思就在这一点上发生,所涵括的范围从日常的阐释学实践(一个外国游客试图用一门他尚未掌握的语言去辨认特定的书写标记,以便找到穿越过这座城市的道路)到人文社会科学系统阐释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基础形式。
当然,一个人的视界和文化经验都不是固定的。正如某个人游览一处风景那样,随着我们穿越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我们经验的视界在不停地改变。个人和文化存在于时间中,这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视界在不停地改变。而当个人或文化发生地理迁移时,其空间视域也随之变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空间都是如此。再者,在时空体(spacetime)的每一瞬间,许多经验和表达方式完全超越了人们和文化的空间与/或时间的视界。在发现美洲之前,欧洲人没有本土美洲人所拥有的任何经验,正如中国人在许多世纪里没有关于非洲文化的任何经验那样。而在21世纪伊始,我们几乎无法进入前历史人类的经验视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不能理解23世纪人类的经验视界,那时人类可能会生活在月球上,甚或由于转基因而变成了不同的物种。在这些情况下,阐释者不仅无法进入不熟悉的视界,而且他往往甚至不能对这些可能的经验视界保持清醒的认识。正如狄尔泰——阐释学的奠基者之一——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生活的表达方式完全陌生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解释。倘若一切事物都不陌生,那么阐释学就没有必要存在(狄尔泰,1914-2005,7:225)[3]。阐释学总是发生于完全熟悉和完全陌生两个极端的间性(in-between)状态之中。当我们面对不熟悉和奇怪的事物时,我们就需要阐释学实践来帮我们克服不解和误解。
由于文化间性的碰撞通常是从不解和误解开始,所以阐释学有望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理解、解释和交流理论的起点。然而,正如前面我的导论所述,我们应该意识到阐释学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话语。在阐释学历史的进程中,不管在其实践还是理论中,阐释学已经发展出不同的形式。以“经验视界”的概念作为起点,我将要在某些方面更深入地讨论前面所提及的阐释学的三个阶段——分别针对视界拓展,视界融合和视界播撒——并且把它们与全球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紧密联系起来。
三. 拓展视界(Widening horizons)
第一种类型的阐释学旨在拓宽经验视界,它在19世纪哲学家如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那里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和系统的发展。然而这种类型的阐释学历史要更为悠久。它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漫长的传统,尤其是与圣经的诠释有着很强的联系。我们同样在许多其他的前现代或传统社会里发现这种阐释学实践,一些权威性的文本(或对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譬如,在中国,我们可以想起儒教和道教逾千年的悠久传统。在这种——通常是相对封闭的——社会中,权威性文本的真理理所当然地被广为接受。可是,由于时间上的距离,这些权威性文本的真理并不是总是易于理解。所以,阐释学诠释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其真理,用于现今的日常生活中。
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将阐释学从专门的神学阐释拓展为文本解释的一种通用的方法。而狄尔泰在其未完成的著作《历史理性批判》(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中,将阐释学改变成为人文科学 (Geisteswissenchaften) 的常规方法。在狄尔泰看来,阐释学的基础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的生活则具有由生活经验(Elebnis)、表达(Ausdruck)和理解(Verstehen)构成结构关系的特性。生活经验设定了主观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我们以此来体验我们的生活。不同于康德的经验(Erfahrung)概念,狄尔泰所言的生活经验(Elebnis)不仅是对世界的一种理论认识,而且也由意志和情感构成(德·穆尔, 2004, 218-283)。
一种获得生活经验的途径就是内省。但是,内省却有其狭隘的限度。不仅由于自我的内省是他人无法达到的,而且由于生活经验具有稍纵即逝的特性,因此即使是对一个拥有生活阅历的人来说,内省都不是一个关于理解的可靠来源。可是,生活经验往往都通过语言的言说与书写,通过姿势和活动,通过人类的艺术品、建筑和社会机构而表现出来。因此狄尔泰认为:“关于生活经验的表达能够比任何内省之所见包含更多的精神生活关系。它来自于生活经验的深层,无需有意识的阐发(狄尔泰,1914—2005,GS 7:206;引述英文翻译:狄尔泰,1985,SW 3:227)。在生活经验中,往往停留在无意识的隐匿关系在它们的表达方式中可以找到清晰的呈现。由于这些原因,可以把表达方式称为创造性的。况且,表达方式不仅能够被理解为他人的精神表达方式,而且它们还有自身独立的存在和意义,神殿、法律和诗歌不仅表现了其创造者的生活经验,而且还表达了具有自身结构与法度的精神结构(GS 7:85; SW 3:106-107)。最终在理解过程中,我们通过将自己(sich Hineinversetzen)置于他者的处境,重新创造(Nachbilden)和重新体验(Nacherleben)生活经验,从而攫住表达的意义。这种生活经验、表达方式和理解能力的阐释学关系,赋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特色,进而建构了人文科学解释方法的基础(GS 7:86-87; SW 3:108-109)。
尽管基督教的释经学遗产在强调揭示真相方面仍然是有迹可循的,但是,生活在自然科学开始控制世界观的时代,狄尔泰却是从客观性维度去解释这种真理的。为了拓展我们自己的视界,阐释学被作为一种科学的解释方法来理解,它演变成一种独白式的活动,一种对陌生经验视界的理论上的重构。按照狄尔泰的看法,阐释学理解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拓展视界而克服我们个体生命的局限性,“理解拓展了我们存在的视界”(狄尔泰, 1914-2005, GS 5:275)。
理解首先克服了个体生活经验的局限性……而延伸到形形色色的人、人类精神的创造和群体,理解就拓展了个体生命和人文科学的视域,开拓了由共同性迈向普遍性的道路(狄尔泰,1914—2005,GS 7:141 引自英译版狄尔泰,2002b,SW3:162)。
对于文化间性阐释学来说,这种阐释学的概念具有何种蕴涵呢?首先,在这种视野中,文化间性阐释学包含了一种理论的重构,它重构了来自于其他文化的人类生活经验,以及他们的文化表达方式,例如文本、科技产品、艺术品、建筑物、风俗习惯以及机构设置等。为了拓展自己(个人与文化的)经验视界,这种文化间性的阐释那时是一种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意义的独白式的努力。我们自己的经验视界既是阐释实践的起点,又是终点。
不言而喻,我们文化视野的拓宽常常是一种在理论、实践和美学上不断丰富的经历。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智慧,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工具和愉悦的体验。它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在相对封闭的(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现在仍是这样)前现代文化里,传统基本上是不证自明的。毕竟,当还没有其他的世界观或者不同的政治体系为人们所知时,既存的世界观或政治体系不太可能会遭到质疑。而与其他的世界观或政治体系相遭遇,可能是推进世界开放的一种重要的动力。
然而,这种独白式的阐释学也有它的陷阱。狄尔泰敏锐地意识到,绝不存在“天真无辜的”理解。因为我们总是从自身限度的视域出发,我们总是试图从自身限度的视界出发,单独对其他的文化进行解释,由此而将“他者”减缩为“同一”。况且,在这些情况下,本土文化往往被设想为优于异域文化。文化际遇和全球化的历史,显示了这种描述与规范种族中心主义的大量的现象。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西方哲学家对中国汉字性质的解释。他们大多数人完全从拼音字母的语音视界来评价中国汉字(张汉良,1988)。比如,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是一个早期对这种争议作出贡献的人。他在168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真正的文字和哲学的语言”的文章,他确信中国汉字“具有很多重大的缺陷”:
这些文字的“字形”是不可思议的复杂和困难。它们除了复杂繁难和令人手足无措以外,在字的形状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之间似乎并无任何相似之处,至于它们之间的契合或对立,也未必有什么可以接受的必要的来历。(威尔金斯,1968, 450)
大约150年之后,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百科全书》(1817)第459条中也体现了一种相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本体论往往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
口语发展的进程大多都紧密地依赖于字母表习惯的书写;正是由此,口语获得了其发音的精确性和纯洁性。中国口语的不完美是声名狼藉的:大量的汉语字词拥有着多个完全不同的意思,可以达到十种或二十种,因此,在口头上,只能通过重音和强度,通过低声而舒缓说话或是高喊来加以辨别。欧洲人学说汉语,在他们掌握这种不合理的优雅艺术之前,会陷进这种极为荒谬的羁绊之中。在此,完美则表现在无重音说话(parler sans accent)的反面,而在欧洲,有教养的人恰是被要求无重音说话的。以象形文字为模式的书写方式让中国口语远离客观的精确性,而拼音文字却能获得这种精确性。(黑格尔,1969-1971,x:274)[4]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像威尔金斯和黑格尔那样对中国汉字加以否定性的评判。譬如哲学家莱布尼兹显然就是一个例外。他认为中文是一门可能会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很好的候选语言,正因为中文没有为口头语言所束缚:
了解中国汉字的那些人有理由相信汉字将会成为世界通用的字符,其书写形式将会被全世界所理解。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够认同某个字符可以指称某种事物,那么每个人就能够通过不同的发音与另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这样我们就能推行一种普世的符号论。[…]如果我们用微小的图表取代字词,从而图画般地表达可见之物,通过与其相关的可见之物表现不可见之物,也能获得适宜传达语形变化与语助词的某种附加的符号。这将即刻会让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同远距离的人们进行交流。(莱布尼兹,1981,290)[5]
乍看起来,莱布尼兹似乎远离了我们在威尔金斯与黑格尔那里所见到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可是,为了品位莱布尼兹对中国汉字的积极评价,我们必须考虑其阐释背后的动力。像威尔金斯那样,莱布尼兹对汉语的兴趣在于以基督教的欲望为动机,发展一门世界性的语言。当然,在莱布尼兹的个案中,他并没有过多地试图去重建存在于巴别塔之前的原始的亚当语言,而是更多地发展了一种未来的普通语言(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这是一种能够表达所有思想概念的“代数学”,它包括一种理性演算(calculus ratiocinator),由一套符号操作规则构成(参考艾柯,1993,第14章)。然而,这种世界语的观念却是深深地扎根于想拥有普世语言的基督教徒的观念中[6]。从这个意义上说,莱布尼兹对于中文的阐释依旧保留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性质。
由于经验视界的基本限度,可以认为种族中心主义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凭借着阐释者的视界,种族中心主义却可以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正如林同济、亨利·罗斯蒙特和安乐哲综观西方对中国哲学的接受时所解释的那样:
然而,西方哲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迥异于中国的对位。中国的种族中心主义没有从传统上否认西方文化,它仅仅是否认了其相关性和价值观。中国的种族中心主义是以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自负的感觉为基础的:中国不需要西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恰恰相反,它要在普世性的主张中树立自己的信念。迄今为止,西方主流哲学家们一直欢迎有机会进入中国哲学,这些哲学家都是带着这种或那种简化论的特性对中国哲学不加区别地予以评判。这种简化论发挥着启蒙运动假设的巨大功用,从笛卡尔时代起,这种启蒙假设塑造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态,通常承载了某些普世论的主张,往往以方法论、索引的面目出现,并且还包括某些更为绝对论的相对主义极端形式,否定了一切能够与之相拮抗的文化。(林同济、罗斯蒙特和安乐哲,747-8)
在此意义上,威尔金斯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他完全基于自己的偏见去看待中国汉字,而莱布尼兹则假设了一个中性而超然的“欧米茄点”,尽管如此,但他最终仍然以一种普世论的基督教真理的名义湮灭了自己的个性。[7]这种对普遍性的渴望也源自于狄尔泰的视界拓展的理念。毕竟,根据我们先前读到的一段引文,这种拓展假设“开拓了由共同性迈向普遍性的道路”。正如狄尔泰所理解的那样,阐释学旨趣在于扩大我们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范围,以便获得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遍性和绝对知识。尽管深受浪漫主义运动影响的狄尔泰承认,在历史世界中“一切理解都难免片面,从来就不可能完成” (GS 5:330; SW 4: 249),但他的调控理想仍然是要将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扩展成为全球视域,包含全人类的经验在内。
4. 四. 融合视界(Fusing horizons)
20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在他们关于理解的哲学反思中把人类限度的概念加以激进化,因此认为,把个人的经验视界拓展到普遍性的层次是无法做到的。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and Methode, 1960) 中详细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发展了另一种形式的阐释学,其要旨不在于视界拓展,而在于视界融合。
在伽达默尔看来,狄尔泰的重构阐释学成了追求客观性的实证论的牺牲品(伽达默尔,1986, 241;伽达默尔,1989b, 237)。在重构阐释学中,阐释者被认为是一个中立的认知主体,其自身有限的经验视界并没有被考虑在之内。因此,狄尔泰成了这种偏见的受害者,这同样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即认为应当不带偏见地作出判断。伽达默尔认为,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这种对偏见的怀疑造成了对事实的误解,即理解总是惟有在对亟待理解事物的某种前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偏见恰是理解之可能性的前提条件。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可能有人会争辩说,伽达默尔不加批判地重复了海德格尔对狄尔泰颇为恶毒的批判,极度夸张了狄尔泰的客观论(德·穆尔 2004,311-325,330-37)。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中,狄尔泰成了敌手的形象,使得他们能够推进自己替代性的阐释学方案。但是事实上,狄尔泰关于生活经验、表达方式和理解之关系的本体论分析,在很多方面预示(和启发)了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分析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当然,这一事实也无法抹杀,伽达默尔的建构阐释学概念在某些方面迥异于狄尔泰的重构阐释学。
不同于狄尔泰颇具独白特性的理解模式,伽达默尔为对话式的模式加以辩护。追溯到柏拉图和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明确指出,把理解加以概念化的适当方式就是会话(伽达默尔,1991,173,163)。在会话中,我们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对我们交谈对象的谈话意思进行心理重构,而在于理解所讨论的事情。
此外,不同于狄尔泰理论性的理解概念,伽达默尔强调阐释学实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阐释学理解总是旨在于实践应用。我们不仅要理解所阐释的事物,而且还要将它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此外,伽达默尔还认为,在全面理解的时间性上狄尔泰也缺乏眼光。文本的意义不是某种客观呈现的东西,而是在理解的历史中所展开的。柏拉图或孔子著作的意义都不能简缩为作者的原始意图或原初读者的生活经验,而是要视之为发生在对他们的阐释史中的一种时间过程。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是一个历史的运动,从来就无法加以完全的客观化,它担负着工作和阐释的双重任务 (WM:306/TM: 301)。效果历史的意识就是对一切个体阐释的根本性限度保持清醒的认识。
还有与狄尔泰不同的是,伽达默尔并不认为诠释者和亟待解释的文本之间的时间或空间距离原来就是障碍,而无宁说这是理解生生不已的源泉。效果历史的概念使我们将理解的对话过程定义为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同上,311/305)。事实上融合的观念体现的不是一种重构而是意义的生产性建构:“这就是为什么理解不仅仅是再生产的,也总是生产性行为的原因。”(同上,301/296)。在经过成功的阐释之后,无论是阐释者还是被阐释的事物都不会与之前一模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视界融合的观念即是误导,因为在效果历史中,并没有两个分离的、封闭的视界,而关键是包含了不同视界的事件(WM:311/TM:305)。
这是一种张力:在传统中,陌生与熟悉之间遇合的嬉戏是特定的中间点,它居于疏远的历史对象和鲜活传统的构成之间。阐释学的真正定位就是这种间性(this in-between)。(WM:300/TM:295)
不同于狄尔泰,伽达默尔颇为关注语言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在这方面追随海德格尔的伽达默尔而言,语言开启我们世界的媒介:“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WM:478/TM:474)。再者,语言也是对话得以发生的媒介。鉴于这种原因,为了共同理解和认可某物,视界的融合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寻求共同语言的尝试:“一切会话都预设了一种共同的语言,抑或更好的说法是,创建一种共同的语言”(WM:384/TM:371)。文字游戏很容易在翻译过程中失去韵味,伽达默尔说:
因此,人们通常能够很快地互相理解(verstehen),或者以趋同(Einverständnis)之心使他们自己得到理解(verständigen sich)。理解(Verständigung)的实现总是在达成对某些事物理解之时。(WM:183/TM:180)
虽然会话伙伴建立了一种在他们对话之前尚未存在的语言,但是它却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我们“都被转移到了一个交流圈,我们在其中无法再保持我们的原样” (WM:384/WT:371)。一种真正的对话
总是会导致擢升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身的特殊性,而且也克服了他者的特殊性。“视界”的概念本身就提示了它的含义,因为它体现了试图获得理解的人所必须拥有的优越的视觉广度。获得视界,则意味着一个人学会超越自己狭隘的视域——不是为了转移目光,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总体格局和更真实的比例中更好地审视它。(WM:/TM: 304)
乍看起来,伽达默尔建构性的对话型阐释学似乎比狄尔泰的重构性的独白型阐释学更有资格适合文化间性阐释学。尤其是它似乎更适合于要应付文化碰撞戏剧性加剧的当代。伽达默尔在《欧洲的遗产》(Das Erbe Europas, 1989)中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际遇不应是忽视成员国之间的差异的一体化,而是我们应该从差异中学习:
这种目的不是(单边地)掌握或者控制,而是我们有责任去体验确实异于我们预判背景的他者的他者性。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所奋斗的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参与他者,分享他者的特异性[……]这样,为了互相分享,我们可以学习把他者性和其他人类作为“我们的他者”加以体验。(伽达默尔,1989a,34)
在同一位印度思想家交谈时,他继续阐发说,这种多元性的统一模式在今天应该“扩展到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印度,还有穆斯林文化。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都会有某种独特之处,可以为人类的团结与福祉作出贡献”(Dallmayr, 2009, 33; Pantham, 1992, 132)。
乍看之下,虽然伽达默尔的文化间性阐释学听起来易于引发情感共鸣[8],但是它似乎忽略了跨文化对话和阐释实践中特有的困难。首先,伽达默尔似乎忽视了在跨文化境遇中经常会出现的不对称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的不对称性。在跨文化际遇中,“会话伙伴”(无论两个人,还是人与文本)常操持不同的母语。在很多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为了寻找或创造一种共同语言,往往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语言进行会话和解释。例如,只有很少的西方人能够说与读中文,所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通常是使用英语,因为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成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交流的国际标准[9]。
然而,语言并非中性的媒介。它们对世界作出不同的揭示、建构和评价。作为“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不同的语言会带来不同的本体论和道义论(deontologies)。但这未必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决定论(如沃尔夫·萨丕尔假说的著名论点),也未必意指根本不可能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可靠的翻译(如奎因的论文《翻译的不确定性》的断言(奎因,1969))。虽然语言不能太多地决定什么能说和什么不能说,但是它们——至少是部分地[10]——构成了我们体验世界的途径。因此,比起那些我们认为曾作出贡献的印欧语系传统的思想家来,汉语给关于这个世界的不同的信仰和态度提供了更多的基础(汉森, 1985)。
让我举例阐明这一点。在查德·汉森(Chad Hansen)的《古代中国的语言和逻辑》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论点,古汉语名词在(通俗)语义学中更像物质名词(如英语中的“水”、“糖”),而不像可数名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汉语的语义理论家倾向于用一种关于现实的总分学的材料总体模式(a mereological stuff-whole model)来组织世界的客观对象(汉森 1983,1998)。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名词的典型功用就是当作可数名词来使用。这就导致了显著不同的本体论的现实模式:
怀揣着可数名词的功能模式和一对一的命名范式,当人们审视世界的结构时,可能会受到鼓舞和触动,认为世界是由一些可数的、自足的事物构成的,无论是在特殊性还是在普遍性层面都是如此。在印欧语系中可数名词的功能模式下,带有如下假设的柏拉图一与多的问题(the Platonic one-many problem)看上去显得很自然的:存在着某种单一、自足的普遍性本质,这个实体是共有的或严格地使所有拥有相同名字的特殊个体相统一。心目中带有这一假设的那些哲学家一直在寻找这种单一的本质,倾向于把它要么与将特殊性实体化的一种本体普遍性(柏拉图式的现实主义或关涉普遍性的其他现实主义版本)相认同,要么与一种精神共享的概念本质(概念主义)相认同。
但是,倘若汉语名词的通俗语义学(无论是伴随聚合名词的功能模式还是物质名词的功能模式)倾向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为基础去组织客观对象,并由此使他们隐含的本体论具有一种总分学的特征,那些使用汉语名词去表达他们思想的中国古典哲学家们将会受到鼓舞,从而用总分学的本体论看待这个世界,而他们将会受挫于把柏拉图的一与多问题与前述的假设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家来说,普通名词根本不会引发柏拉图式的一与多的问题。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柏拉图一与多的经典问题一直没有被有意识地置入中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原因,并且一般来说,中国哲学家似乎对于相关本体论问题的争辩不太感兴趣(Mou,1998)。[11]
因此,当中西哲学家用英语进行跨文化对话或者当一个西方哲学家解释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英译本时,问题在于,这是否能够真正地导致一种本体论的视界融合,迈向“更高程度的普遍性,不仅能克服我们自身的特殊性,而且还能克服他者的特殊性”[12]。无宁说,在这些情况下,一种视界似乎会被归纳到另外一种视界。按照伽达默尔的批评家的观点,这种风险就内在于效果历史的概念。人们很难避免这种印象,在伽达默尔的建构阐释学中,效果历史被指派了黑格尔包罗万象的绝对精神的角色。这就使得他的阐释学对话视野有所贬值:“因此,效果历史的推测性对话最终变成了辩证法的一种推测性对话的独白版本”(弗兰克,1989)。
如果存在着某种附加的不对称性,牵涉到文化、文化欲求和不同文化“对话”的目标之间的权力关系,那么,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前面我已提到这种事实,由于对西方思想的优越性和/或普世性抱有种族中心主义的信仰,所以西方哲学家往往会忽视中国哲学。在西方语言生产与驾驭所需知识比第三世界语言更加容易的情况下,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往往无法忽视西方文化(Asad,1986)。虽然正在变化的权力关系和不断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可能改变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本质,但是在这个历史时刻,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非对称性:
当西方的汉学家发现中国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时,他们很少发现应该用中国模式对西方进行迫切的改造。相反,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倒是将西方的伦理、技术、经济前景作为真实的选择来感知,甚至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最佳的和唯一的选择.(Chew,2009,38f)
莱布尼兹与(中国)阴阳原则的跨文化际遇的历史,为这种非对称性“对话”提供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在前述他寻求一种通用语言的语境中,莱布尼兹还致力于创建一种机械计算器。可是,应用十进制来造这种计算器则需要很多零部件。由于这个原因,在《二进制算数的阐释》( Explication de l' arithmetique binaire, 1703)中,莱布尼兹开发出一种二进制,这就使得一种更简单的制造成为可能。莱布尼兹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他的二进制与构成《易经》64卦的阴阳二元代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13] 在他的信件里,莱布尼兹甚至赞扬《易经》——这本书可能是传教士闵明我(the Jesuit Claudio Grimaldi)介绍给他的,闵明我在北京生活过十七年,莱布尼兹在意大利的旅途中和他相遇——是他重要的灵感来源(莱布尼兹,1976-2004)。尽管如此,莱布尼兹却宣称对卦的真正解释来源于欧洲人。[14]而实际上,这种“视界融合”无宁说是从普遍性视野对卦的一种阐释,再度显示了从建立通用语言的角度对卦的硬性解释——经过多个世纪的发展和磨合——最终导致了数字化二进制电脑的发明,带来了“世界观的信息化”和全球性的“信息时代”。(参见德·穆尔 1999,2007,2010年)
5.播撒视界(Disseminating horizons)
在跨文化阐释学中,重构与建构方案的实践与理论陷阱催生了第三种类型的阐释学。雅克·德里达的解构论堪为其中最负盛名的代表。由于这种“解构阐释学”质疑视界与理解的概念本身,因此某些人会迟疑不决,根本不想把这种理论方法称之为阐释学,他们甚或情愿称之为一种反阐释学。德里达把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的论题加以极端化,认为阐释学是建立在某种必要的非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施莱尔马赫,1985,1271)。按照施莱尔马赫的看法,任何词语皆没有固定的意义。其意义依赖于它所呈现于其中的语境或视界。不过,这种视界可以向四面八方拓展,没有终结。对施莱尔马赫而言,这种阐释学的理解方式不啻为一项无穷无尽的任务。德里达把这种深刻的见解进一步推进,认为在对任何一种意义的界定中,皆会对某种根本无法决定的事物作出决定。况且,每一个词语都可以被抽绎出它“原来的”语境,转换到另一个语境。通过引用一个词语或一段较长的文句——德里达采用把一个词语“嫁接”到另一“枝条”的意象——新的意义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每一个符号,无论是语言学的还是非语言学的,口头的还是书写的(在这一命题的通常意义上),作为小的单元还是大的单元,都可以引用,置入引号之间;由此,它可以打破种种给定的语境,以一种绝对不饱和的形态生发出无限的新语境。这并不意味着该标记在其语境之外是有效的,而是相反,只存在着没有任何绝对停泊中心的语境。这种引证、复制或两重性,这种标记的可重复性,并非是意外或异常,而是(正常/反常)若没有它,一个标记甚至不可能具有所谓的“正常”功能。(德里达, 1972b, 320-1; 德里达, 1982, 381)
德里达的解构阐释学之目的并不是要揭示人们所期许的各种文本丰赡的意义,而是要质疑阐释学理解的可能性:
惯常统制着交流观念的语义学视界被书写的介入所超越或削弱,这就是一种播撒,无法简缩为意见分歧。书写被阅读,而且在“最终的分析”中并不导致阐释学的辨读,并不引起意义或真理的解码。(德里达, 1972a, 294; 1972b, 392; 德里达 1982, 329)
若继续以视界的意象为基础(在上述引语中德里达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就可以认为,当他以播撒(dissemination)来反对意见分歧(polysemy)时,德里达的目的不在于视界的拓展(如同狄尔泰那样),也不在于视界的融合(如同伽达默尔那样),而在于视界的播撒。德里达似乎要推进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多边会谈,以取代独白或者对话。
狄尔泰的重构阐释学是理论性的,伽达默尔的建构阐释学是实践性的,而德里达的解构阐释学的目的则无宁说是一种关涉意义的无止境的审美嬉戏。况且,这种嬉戏绝然不乏严肃性。德里达认为,拒绝把某种确定的意义指派给文本或谈话伙伴的言论,是一种尊重“他者的他者性”的行为。倘若一切理解的阐释学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欺压他者的暴力行为,那么,德里达就会——采用爱德华·格利桑(Éduard Glissant)的用法——为“不透明的权利”而辩护(参阅de Schutter, 2004; Glissant, 1997, 29)。我们发现它在抵抗某些群体加入那种通常是暴力的、赋予全球化进程以特性的“人类会谈”中得到了表达。[15]然而,德里达的方案并不是一种辩护的方案。其解构论有一种“让完整的他者之冒险或呈现来临”的承载 (德里达, 1987, 61)。由此,德里达使得他的解构阐释学包含了对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
这种努力的艰难窘境在德里达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1967)与汉字的遇合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部著作中,德里达旨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降,逻各斯中心主义赋予西方形而上学以特色。而逻各斯中心主义最令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语音中心主义:这种观念意味着逻各斯真理只能在说话中找到,而书写则是第二位的与从属性的。在前文对黑格尔批判中国文字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触及了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尽管拼音文字的地位要低于说话,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它的语音形式至少赋予它一种明显与口头语言相关的类似性。鉴于这个原因,拼音文字要优于汉字,因为(汉字)这种文字完全缺乏与说话的亲密联系。[16]
德里达批判这种具有西方形而上学特征的等级制二元对立,如内/外、自我/他者、男性/女性、说话/书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他的观念中,黑格尔对中文书写的激进的反对与莱布尼兹夸张的崇拜一样,都是萦绕着西方形而上学的种族歧见(参阅张汉良, 1988, 及尾注5; 德里达, 1976, 78)。而德里达则旨在通过解构它们的对立性而瓦解等级制的二元对立。
譬如,当我们更紧密地审视文化差异时,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就会有问题。每一种文化都从其他文化获取众多元素。举例来说,当我们的郁金香被作为传统的荷兰之花时,人们通常都忘记了,这种荷兰的意象却是来自于土耳其与阿富汗。而当通心粉被全世界认为是典型的意大利食品时,我们应当记得,它是数世纪前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从这些例证中,我们可以明白文化并非是关于传统、观念、商品和规范之同质的、自足的和不变的整体。当诸元素从一种文化转入另一种文化时,这些元素就被嫁接到了新的文化语境并获得新的意义。对那些“援引”其他文化所固有的可引用元素的人而言,这些“异邦”元素很快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虽然意大利人无疑会把通心粉视为他们文化身份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却要牢记,通心粉的意大利特性受惠于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于它在中国与意大利的菜肴、文化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甚至能够说,每一种文化本身早已是文化间性的了。任何文化的“渊源”总是存在于“其他地方”。若无这种间性维度,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嬉戏是不可能的。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本人似乎回归到了他旨在解构的那种同样的等级制二元对立。在他抵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十字军征伐中,德里达——不像莱布尼兹那样——无法抗拒一种夸张的对汉字的崇拜,他称之为“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文明发展强力运动的明证” (德里达, 1976, 90, 着重号系约斯·德·穆尔所加)。或许恰恰是他对“他者的他者性”的迷恋,这才诱使他完全没有注意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就不仅完全忽视了汉字书写具有大量的语音元素的事实,而且也没有意识到语音中心主义在中国经典和现代语言学中远非无迹可寻。[17]有鉴于此,Sean Meighoo关于德里达之中文书写概念的广博分析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德里达自己的中文书写概念发挥了一种欧美‘幻觉’的功能,这是他无疑与莱布尼兹……共享着的一种幻觉。这种中文书写的概念仍然保留着‘本国的表现形式’,隐含着对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的严重的‘误解’。” (Meighoo, 2008)
尽管我们可能无法将这种例子普适化,但是,即便是像德里达这样的解构哲学家在此个案中也未能成功地避免(一种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这种事实势必要迫使我们降低对完美无暇的跨文化对话和阐释学之可能性的期待。我们是否应该强化施莱尔马赫的命题,即一切阐释皆基于非理解(non-understanding),也无可避免地在不理解中延续,并且得出结论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际遇注定要失败甚或导致“文化的冲突”(亨廷顿,1996),至少在理解(understanding)的层面上是如此?抑或我们已经进入的全球化的后现代阶段,也显露出了跨文化对话与阐释学的一种新的、尚未预知的阶段?
6.万花筒视界(Kaleidoscoping horizons)
在前面关于重构、建构和解构阐释学的讨论中,我强调了“视界”概念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跨文化理解概念的每一个阶段,不同(文化)视界的存在构成了理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条件。即使是在德里达的个案中,视界的播撒亦预设了它们的存在。视界本身倾向于起着牢狱的功能,无可避免地迫使它们的囚卒进入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类生命形式的限度之不可分割的样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中心主义本身是我们应当加以妖魔化的事物。某种(无可避免的种族中心主义)视界不仅是一种障碍,而且也恰是理解与交流的可能性的条件。这是一种意义丰赡的关联域,倘若没有它,则根本不会有理解或者交流。正如我们所见,跨文化阐释学的每一种类型都有其优点。凭借着重构以及与其他经验视界的合作拓展我们的视界,由此丰富我们的生活。在视界的融合中,我们建构新的知识,展开新的实践。解构现存的视界,可以为其他的可能性创造开放的空间。甚至当跨文化理解与交流导致对他者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误解或错误传达时,在很多情况下,这将会更偏爱完全陌生的经验和对他者的纯粹误解。况且,误解往往是富于生产性的。毫无疑问,并非是所有的误解都是人们想要的。误解易于导致各式各样的紧张关系与冲突斗争。然而这些紧张关系与冲突斗争却是驱动人类历史“引擎”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者,我们不应该夸大“视界冲突”。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深入检视的情况下,视界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浑然一体的。实际上,我们生存在一种多元的视界中:伦理学、语言学、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宗教、政治、哲学、情感、社会、经济、科学,无数的视界围绕着并且建构着我们,这里仅仅提及少数视界。有些视界颇为狭窄与特异,另一些视界几乎是世界性的。理解一种外语会话可能会行不通,而去理解异域文化的那种父母失子之痛的哀伤却并不困难。尽管可能会有巨大的文化鸿沟横亘在沙特阿拉伯女性与加拿大女性之间,但是,作为女性她们都生活在往往是由男性统制的世界里,她们可以同时共享一种特殊的经验视界。而北京出租车司机与柏林出租车司机的经验视界,可能要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与北京的大学教授的经验视界更具有共同性。
况且,在全球化的后现代阶段,人员、观念、习惯与商品的流通和交流的势头汹涌,置身于其中,浑然一体的视界概念已经变得完全失效。成千上万的移民、打工者、学生和旅游者在不同的文化中移动。土特产正在全球配送。思想观念通过全球电脑的互联网而流转。世界居民日益增长的数量正在生成混杂的、属于多种不同视界的主体。这种“真正的混杂”是居于众多不同的视界之间的(鲍曼, 1991, 58)。这种混杂的主体性是后现代全球化的典型表征。
尽管全球化与人类同样的古老,但是,前现代文化通常是单一文化的,在此意义上,它们相对匮乏交通与通讯工具,因此,流通与交流的步伐往往迟缓。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则多为多元文化。在现代社会里,众多不同的文化在同一地方毗邻而居。在现代文化中,新移民常常被视为陌生人,虽然身体上接近,但是在社会上与文化上却是遥远的(Marotta, 2009)。后现代的全球化,由形形色色的信息与通讯网络构成,情境特色亦不相同,我们可以在身体上是遥远的,但是在社会上与文化上却是接近的。我们是文化间性的,因为我们是不断流通与交流过程的组成部分。[18]
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个人与文化的视界日益变成万花筒式的视界。后现代文化具有数据库的特征,数据库可以对人类的“mentome”元素和全球文化的“基因池”进行不断地组合、重组和解构组合。在这种万花筒式的体验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日益变得模糊不清与模棱两可。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因为在我们的当代世界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视界同时存在,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互相影响。
这种复杂并且往往是混乱的情境对文化间性阐释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视界的阐释学重构、建构与解构无疑将会延续。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尽管它们是无法协调的概念与解释实践,但是我们仍然与它们同时生活在一起,因为在彼此解释的实践中,它们不断要互相加以预设。尽管如此,我们视界的万花筒化将会迫使我们发展出新的策略,从而理解与解释彼此以及我们自身。
由于我们(目前的)生命形式在根本上的有限性,想要克服种族中心主义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期冀在文化间性的阐释学中实现(或至少是作为其调整的理想来珍视)的,是一种“反思种族中心主义”(reflective ethnocentrism)。[19]恰如我们可以期冀在对往昔的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实现“反思时代错误”(reflective anachronism)。毫无疑问,对阐释学而言这是一个永不完结的任务。而没有终结也意味着拥有未来。
后像(AFTERIMAGE)
图一. 徐冰《天穹之书》(Book from the Sky, 1987-1991)。混合媒体设置。加拿大国家画廊,渥太华。
图二. 徐冰《新英文(方块字)书法》
图三. 徐冰“纸本水墨”方块字书法,2005.
图四. 徐冰《大地之书》(Book from the Earth, 2008) 图五. 徐冰《大地之书·小说》(2008)
不言而喻,对文化间性阐释学的反思并非是哲学家独享的特权。它也是当代艺术中循环不已的主题。在前述分析的语境中,中国艺术家徐冰(1956)的作品尤其令人兴趣盎然。徐冰1970年代曾经在北京艺术中心研究机构受过训练,那时社会现实主义仍然是主流传统,他的《天穹之书》(1987-1991)的设计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它由数千个仿制的汉字构成,艺术家精心手工刻成积木,用来设计成为移动型的活字印刷的卷轴,铺设在地板上和悬吊在天花板上加以展示,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混合媒体设置(见图一)。尽管这一作品因展示空虚的内容而曾经被令人信服地解释为自主性艺术和/或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彭锋,2009),但是它似乎也包蕴了对人类表达方式的深不可测特点的更普遍的反思,所导向的是一种基本的非理解性。徐冰似乎是通过创造汉字把非理解性的体验加以激进化,尽管乍看之下,它们模样相似(它们表达了汉语特性),但事实证明,它们完全是无法阅读的,不仅对于非汉语的读者如此,而且对于汉语读者来说也是这样。虽然硕大的文本平面看来表达了古代智慧,但实际上却充满了秘奥难解的意味。它构成了一种无法穿透的经验视界,对阐释学理解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后来的《方块字书法》(Square word calligraphy,1994-1996)的设计中,徐冰通过探索英汉视界融合的可能性,似乎表达了关于理解的一种更为乐观的愿景。如同《天穹之书》那样,《方块字书法》给人的印象是由汉字构成的,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见图二与图三)。在这一个案中,“字符”实为英语文字构成,但按照中国文字的样貌排列。在此意义上,它们是两种语言学视界的融合。这种设计似乎是关于非对称性的一种幽默评价或批判,恰如我在前文所认为的那样,非对称性常常是视界“融合”的特征(例如,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英国人之间用英语讨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了弄懂《方块字书法》,中国的使用者仍然不得不去学习英语,而英语的说话者则至少须得去熟悉汉字书写的某些特点。正如徐冰所阐释的,这是一种“间性体验”的效果:
方块字书法……靠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之边界线生存。对于来自这两种文化的观察者来说,这些字符显示了既熟悉又陌生的相同点。中国人认得出这些字符熟悉的容貌,但是却弄不清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对于西方人而言,它们乍看之下是来自亚洲文化的字型,然而最终却是能够阅读与理解的……方块字书法的荒诞性在于,它从毫不相干的两种语言系统中抽绎出两种不同的文字,并且将其融为一体。倘若你采用现存的汉语或英语概念去试图阅读或者解释这些字符,那么你无法获得成功。这种外貌与内质之间的全然分离,把人们置于一种移动性的文化位置,一种不确定的过渡状态(引自彭锋, 2009, 4-5)。
在近期的《大地之书》(Book from the Earth,2008)的设计中,徐冰似乎是给予了追求普适性语言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痴迷以讥评。该作品由电脑程序完成,可以把汉语和英语迻译为一种普适性的图像语言,其灵感受启于可以在国际机场找到的那种图像类型(图四)。电脑程序使得各自操持不同语言的中国人与英国人能够用一种视觉方式进行交流。尽管在访谈中徐冰宣称“该设计意在使得交流得以实施,而无需考虑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或者教育水平如何”,甚至提出“这种趋势的拓展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引自彭锋,2009, 7),与此同时,该作品似乎还包含了一种讽刺性的反思,针对的是那种发展明晰无瑕的语言的野心。《大地之书》可以成功地将基本信息与故事进行交流,而徐冰在像《小说》这样的作品中试图传达更为复杂的意义(图五),这使得我们不仅意识到我们有限的自然语言的丰富性,而且同时划分了文化间性的对话与多方会谈无法超越的界限。
参考文献
Asad, T. (1986). The inequality of language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uman, Z.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l. (1988). Hallucinating the Other: Derridean Fantasies of Chinese Script (Vol. Working Paper No. 4). Milwauke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Center for Twentieth-Century Studies.
Chew, M. M. (2009).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ve Difficultie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 Hermeneutical View. Asian Culture and History 1(2), 34-44.
Dallmayr, F. (2009). Hermeneutics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Ethics & Global Politics, 2(1), 23-39.
De Mul, J. (1999).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he worldview.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 604-629.
De Mul, J. (2004). The tragedy of finitude : 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 Mul, J. (2007). 赛 博 空 间 的 奥 德 赛]. Guangxi Norm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De Mul, J. (2010). Cyberspace Odyssey: Towards a Virtual Ontology and Anthropology.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De Schutter, H. (2004). Gadamer and Interculturalism: Ethnocentrism or Authenticity. In D. Powell & F. Sze (Eds.), Interculturalism. Exploring Critical Issues (pp. 51-58).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Derrida, J. (1972a). La dissémination. Paris.
Derrida, J. (1972b).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82).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rida, J. (1987). Psyché : inventions de l'autre. Paris: Galilée.
Dilthey, W. (1914-2005). Gesammelte Schriften. Stuttgart/Göttingen: B.G.Teubner, Vandenhoeck & Ruprecht.
Dilthey, W. (1985). Selected work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ilthey, W. (2002a).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ilthey, W. (2002b). Selected works. Volume 3: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ences (Vol. 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co, U. (1993). La ricerca della lingua perfetta nella cultura europea. Bari: Laterza.
Frank, M. (1989). What is neostructur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adamer, H.-G. (1986).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WM). In Gesammelte Werke I. Tübingen.
Gadamer, H.-G. (1989a). Das Erbe Europas : Beiträge (1. Aufl. ed.). Frankfurt am Main: Suhramp.
Gadamer, H.-G. (1989b). Truth and method (2nd ed.). New York: Crossroad.
Gadamer, H.-G. (1991). Die Hermeneutik und die Diltheyschule.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Vol. 3, pp. 161-177).
Gilbert, A. L., Regier, T., Kay, P., & Ivry, R. B. (2006). Whorf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in the right visual field but not the lef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amy of Sciences, 103(2), 489-494.
Glissant, E. (1997). Traité du tout-monde. [Paris]: Gallimard.
Hansen, C. (1983).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ansen, C. (1985).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ut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3), 491-519.
Hansen, C. (1997). Do Human Rights Apply to China?: A Norma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Difference. In L. a. Y. Lieberthal, eds. (Ed.), Constructing China (Vol. XLIV, pp. 83-96).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nsen, C. (1998). Zhongguo gu dai de yu yan he luo ji (Di 1 ban. ed.).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 jing xiao Xin hua shu dian zong dian Beijing fa xing suo.
Hegel, G. W. F. (1969-1971). Theorie Werkausgabe. Frankfurt a/M.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Leibniz, G. W. (1703). Explication de l' arithmetique binaire.
Leibniz, G. W. (1976-2004). Mathematisch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und technischer Briefwechsel (Vol. III). Berlin: Leibniz-Archiv Hannover.
Leibniz, G. W. (1981).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Eng.]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ibniz, G. W. (1990-2008). Mathematische Schriften (Vol. VII). Berlin: Leibniz-Archiv Hannover.
Lin, T., Rosemont, H., & Ames, R. T. (1995). Chinese Philosophy: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State-of-the-Ar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3), 727-758: .
Marotta, V. (2009). 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 and the Cross-cultural Subject Export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30(3), 267-284.
Meighoo, S. (2008). Derrida's Chinese prejudice. Cultural Critique(68), 163-209.
Michelfelder, D. P., & Palmer, R. E. (1989). 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ou, B. (1998).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Ontological Insights: A Collective-Noun Hypothesis, Padeia. Comparative Philosophy. Papers poresented at the Twentie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August 10-15, 1998.
Pantham, T. (1992). Some Dimensions of the Universality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 Conversation with Hans-Georg Gadamer. Journal of 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9, 132.
Peng, F. (2009). Art in and out of Cultural Borders: Seeing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from Xu Bing’s Works In J. de Mul & R. van de Vall (Eds.), Gimme Shelter: Global Discourses in Aesthetics Online Series in Aesthetics.
Powell, D., & Sze, F. (Eds.). (2004). Interculturalism: Exploring Critical Issues.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Quine, W. V. (1969).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hleiermacher, F. D. E. (1985). "Allgemeine Hermeneutik" von 1809/10 (Hrsg. W. Virmond). In K.-V. Selge (Ed.), Internationaler Schleiermacher-Kongreß Berlin 1984 (pp. 1271-1310). Berlin/New York.
Wilkins, J. (1968). 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1668). In P. Scolar (Ed.), English Linguistics 1500-1800. A Collection of Facsimile Reprints (Vol. 119). London: Royal Society.
1 本文系提交“传统与当代世界”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9,12,12—13。
[3] 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段名言其实是狄尔泰从施莱尔马赫摘录的笔记系列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在英译本中被省略了(见狄尔泰,2002a,246,注13)。但是,这段引言却是整个阐释学传统的起点。例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中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点:“阐释学的运作是以熟悉和陌生之间的极性为基础的 。” (伽达默尔,1986,295;引自英译本:伽达默尔,1989b,301,295)。
[4] 引自威廉·华莱士的在线翻译: http://www.class.uidaho.edu/mickelsen/ToC/ Hegel _-_Philosophy_of_Mind.htm
[5] 不应感到惊奇,黑格尔在他关于中国语言优点和缺点的讨论中广泛地批评了莱布尼兹对中文的评价:“在谈到口头(这是原始的)语言时,我们仅可以顺便接触到书面语言在特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这要借助于外部的实践活动。正是源于书面语演进依赖的直接的空间直觉领域,人们才采用与生产了符号(454节)。特别是,象形文字使用空间想象以指明概念;而另一方面,拼音文字则用它们来指定已经是符号的口头记录。因此,拼音文字是由符号的符号所组成的——口头语言的文字或具体符号被作为简单元素来分析,分别承载了指定功能。莱布尼兹的务实心态误导他夸大了一种完备的书面语的优点,这种书面语塑形于象形文字的方法(而即使已经有了拼音文字,有如我们称谓数字、行星或化学元素等的符号,象形文字还是要被使用的),可以作为一种通用语,让不同国家,尤其是学者们用来进行交流。[……]惟有静止的文明,例如中国,才承认象形文字的语言是通用国家的; 而且它的书写方法只能是一个独具精神文化的国家的小小构成部分。” (引自威廉·华莱士的翻译:http://www.class.uidaho.edu/mickelsen/ToC/Hegel_-_Philosophy_of_Mind.htm)
[6]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1967)中论述说,莱布尼兹关于汉语这种通用语概念的阐释,“总是导向无限性的神学,导向逻各斯或对上帝无限性的理解”。他还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莱布尼兹关于建立非语音基础的世界通用文字的方案无论如何也无法动摇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原因,尽管它面貌相异,并且充满诱惑,可以在我们的时代进行合法的实践。”(德里达,1976,78)至少,我们能够补充说,它没有搅乱普救论(universalism)。正如我们将在第五节所见,德里达本人确实宣称说,汉语从根本上搅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7] 关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深入分析,参阅:Helder De Schutter的《伽达默尔与文化间性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或真确性》(“Gadamer and Interculturalism: Ethnocentrism or Authenticy”见:de Schutter,2004,51—58)。
[8] 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并非是所有的视界融合都易于引发情感共鸣。譬如,我们可以想一想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与七十年代恐怖运动如红色旅的视界融合,它导致了最近十年的穆斯林暴力恐怖主义。
[9] 这也具有所有的种类的效果。例如,韩国大部分学生曾经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习,而现在只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出于这个原因,如今他们只能通过英文翻译才能了解亚洲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中文)的组成部分。
[10] 在最后数十年里,沃尔夫-萨丕尔的假设已经遭到很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可是,最近关于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似乎在这种假设的修订版提供了支持(Gilbert, Regier, Kay, & Ivry, 2006)。
[11]例如,这可能影响有关人权的讨论。根据现行的本体论,这些权利可以作为占主导地位的个体或社会的权利来加以阐释(汉森,1997)。这体现在1993年的曼谷宣言里:“要认识到,虽然人权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但是必须在一种动态与发展的国际准则制定的语境中对它们加以考虑,要牢记国家和区域的特点,以及各种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性。”不应该阻止我们批评违背普遍人权的政府、社群或者是个人,但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应努力避免那种说教腔调,这种腔调源于我们自己的特殊性与背景是与普遍性相一致的观念。
[12] 尽管伽达默尔承认了翻译的问题,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把它真正地当一回事:“如果我们正在处理一门外国语言,那么,文本将成为语法或语言学解释的对象,但这只是一种初步的情况。理解的真正问题明显出现在这种时候,当要努力理解它所说的内容,提出这种思考的问题时:他如何得出这样一个看法?”(WM:184 /TM:181)
[13] 莱布尼兹在论文《二进制算数的阐释》中概述说:“在这种(二进制)计算中如此惊人的是,这个由0和1组成的算法恰好包含了一个名叫Fohy(伏羲) 的中国古代国王兼哲学家关于线的秘密,伏羲被认为是生活在4000多年前的人,他被中国人认为是他们的帝国和科学的奠基人……”(莱布尼兹,1703)。
[14] “或许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失去了伏羲的图画或标线的意义,他们曾经写下了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评论,寻找我所不知道的意外之旨,所以现在他们关于这种内容的真正解释是来自于欧洲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大约两年多前,我致信给在北京居住的法国著名耶稣会神父白晋(Bouvet),提到我采用的0与1的计数法,只不过是想让他知道这就是释读伏羲图形的关键。在1701年11月14日白晋写给我的回信中,他寄给我这个哲学国王的重要图形,它多至64卦,我们阐释的正确无容置疑,所以可以说,这位教父借助与我的沟通,破译了伏羲之谜。鉴于这些图形可能是世界上所存在的最古老的科学纪念碑,因此在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间隔之后复归其本意,将会显得更加的令人惊羡。”(莱布尼兹,1990-2008,vll:226-7).
[15] 德里达在与伽达默尔1981年在巴黎著名的“争论”中,遵循的也是这样的策略。伽达默尔试图与德里达进行会话,而德里达则故意地规避伽达默尔这些争取互相理解的尝试(Michelfelder & Palmer, 1989)。
[16] “总之,拼音文字更为睿智:在拼音文字中,字词——尤其是对智力而言,这种模式最能恰如其分地用声音表达概念——作用于意识,构成一种反思的对象。它引发睿智的关注,可以被加以分析;制造符号的工作被简缩为其少许简单的元素(清晰发音的主要姿势),由此,说话的情感因子被塑形为普遍性的形式,与此同时,在这种基本阶段它完全获得了精确与纯净。因此,这种拼音文字同时保持了口语的优势,概念与名称严密吻合:名称就是抽象概念的简明符号,也就是说,是简单明晰的概念,无法分解为它的诸特性并且从中进行组合。相反,象形文字并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源于情感符号的直接分析,它起因于对概念的先行分析。因此,可以轻易地提出一种理论,即认为一切概念都可以简缩为它们的元素,或者简单逻辑的术语,所以从表达它们的元素符号中加以选择[……]可以由它们合成而产生一个象形文字系统。”(引自威廉·华莱士的翻译: http://www.class.uidaho.edu/mickelsen/ ToC/Hegel_-_Philosophy_of_Mind.htm)
[17] 正如张汉良在《致幻他者:德里达的汉字幻想》中所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国版可以从6世纪刘勰下面的话中瞥见,他是最早且可能是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惟一系统的文学批评家:“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道以垂文,文以明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 [……]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暴政下,书写被弃为第二性和从属的。在亚里士多德《论解释》的著名开端句子中:“口头词句是精神经验的符号,而书写词句是口头词句的符号。”[……]这种公式,德里达曾在《哲学的边缘》中斥之为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几乎是刘勰释义的翻版:“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因此,在中西方,至少在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传统中,书写的范畴仅仅是记录在与言说和书写主题的关系中(张汉良, 1988, 6)。
[18] “为什么是文化间性论(interculturalism)而不是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的问题?多元文化论是基于个人自主权观念的一种政策。相反,文化间性论则认识到,在一个混合了种族、文化的社会中的行为是多元取向的。多数或大多数文化受到移民或少数族的影响,反之亦然。多元文化论趋向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文化间性论则承认并促使文化的流通、交换、循环、改善和进化成为可能”(Powell & Sze, 2004, 1)。
[19] 这个短语曾经由卜松山(Karl-Heinz Pohl)2009年12月12-1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传统与当代世界”研讨会的讲演《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反思跨文化对话方法论》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