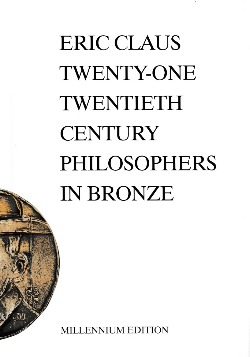Jos de Mul. [荷兰]约斯·德·穆尔:《数字化操控时代的艺术作品》,吕和应译,《学术研究》(广州),2008年第10期,第132-140页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combination", translated by Lü Heying,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Guang Zhou), 2008, No.10, p. 132-140.
约斯·德·穆尔 (荷兰 鹿特丹 伊拉斯谟大学,国际美学会主席)
吕和应 译 (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1. 导论
艺术家总是在利用媒体(media),不管是那些创作壁画的史前绘画者,还是那些依靠计算机技术工作的新媒体艺术家。在此处作广义使用的媒体,意即“传达信息的方式”[1],它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手段而已。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起,我们知道了,经验是由感性的诸形式和人类知性的诸范畴组成和构造的,而在哲学界所谓“语言学和媒体转向”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媒体对塑造人类的心灵和经验起着关键作用。媒体是各种界面,不仅是我们与世界(命名)、还是我们与同伴(交流)以及我们与自身(自我理解)的中介。审美经验也不例外:艺术媒体也是不仅构造艺术家的想象力、也是构造艺术品和审美接受的界面。[2]
为了推进上述反思,文中我会分析计算机界面如何组成和构造审美经验。我的出发点是沃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该文于1936年首次以法文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在这篇划时代的随笔中,本雅明考察了机械复制如何改造了艺术品。他认为,在此本体论改造中,膜拜价值(cult value)已被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取代,而前者曾是古典的、奥若蒂克式的(auratic)艺术品的特征。拙文会证明:首先,在数字化重组(digital recombination)时代,数据库构成了艺术品的本体论模型;其次,在此转变中,展示价值正被我们所谓的操控价值(manipulation value)取代。
我的论述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我将从细部讨论本雅明的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的观念。第二部分,我将把数据库作为范式模型,勾勒出创建计算机对象(computational object)的基本操作。第三部分,我将解释为什么说数据库从本体论上把以展示价值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品转变为以操控价值为特征的后现代艺术品。我将简单讨论荷兰艺术家Geert Mul的两件媒体艺术品来说明我的论证。
在开始第一部分前,我想简单评论一下本雅明这篇随笔的论域(scope)。尽管本雅明作品的标题声称是对艺术的分析,但其实际论域要广得多。它也是一篇关于经济、政治和宗教的随笔。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篇随笔联系这些领域和其他一些领域,分析了一种根本的本体论转变,即人类经验的改变,而人类经验的改变与自然和文化的复制品的机械化过程紧密关联。同样,我在数字化重组时代继续本雅明的分析,论域将超出艺术或美学。本文还要分析自然和文化的数字化操控,它是当前“信息时代”的特征。[3]
2.膜拜价值 vs. 展示价值
尽管在这篇随笔的开头,本雅明强调了艺术品在原则上总是一再被复制,例如,他谈到制作艺术复制品的实践,但他认为机械复制品还是表现了一些新东西。尽管古希腊人已经知道了铸造和冲压的工序,但随着木刻画、雕版画和铜版画在中世纪的出现,平版印刷术在19世纪初的出现,机械复制变成了首要的艺术技巧。然而,只有当摄影和电影的发明和迅速传播,机械复制才变成占统治的文化界面。
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艺术品类型,其特点是时空上的独一无二性(Einmaligkeit)和独特性(Einzigkeit)。原始的艺术品是即时即地的。“就算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缺乏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4]《蒙娜·丽莎》是唯一的,我们想看该画,就得去巴黎卢浮宫。

图一:参观者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挤成一团
在本雅明看来,艺术品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构成了历史,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这种历史。例如,其中包括,岁月引起的物理构造的改变和所有权的变更。
前一种变化的痕迹只能由化学或物理分析方法去发掘,而这种分析并不适用于复制品;至于后 一种变化的痕迹则是个传统问题,要弄清它,必须从原作的状况入手。原作的即时即地性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它自问世那一刻起可继承的所有东西,包括它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证据。[5]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其材料和历史的原真性(Echtheit)及权威性,本雅明用另一个词“光韵”(aura)来命名。光韵附身,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就能轻易变成巫术或宗教膜拜的对象。维纳斯雕像在古希腊是崇拜对象,以此为例,本雅明指出:
我们知道,最早的艺术作品起源于某种礼仪——起初是巫术礼仪,后来是宗教礼仪。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艺术作品那种闪发光韵的存在方式从未完全与它的礼仪功能分开。换言之,“原真”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独一无二价值植根于神学,这个根基尽管辗转流传,但它作为世俗化了的礼仪在对美的崇拜的最普通形式中,依然清晰可辨。[6]
在一个脚注中,本雅明引入了一个概念: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膜拜价值,并把它及其光韵联系起来。在此情形下,他也对后一概念做了有趣的界定:
把光韵界定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无非体现了在时空感知范畴中对艺术品膜拜价值的描述。远与近是一组对立范畴。本质上远的东西就是不可接近的,不可接近性实际上就成了膜拜对象的一种主要性质。膜拜形象的实质就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一个人可以从他的题材中达到这种贴近,但这种贴近并没有消除它在表面上保持的距离。[7]
要是我们模糊年代,把新媒体研究的关键概念应用于本雅明分析,我们也许会说,奥若蒂克式的艺术品,是感性成分与超感性成分之间(即艺术品的物质材料与其富含意义的历史之间)的界面。光就物质材料来看,奥若蒂克式的艺术品也许触手可及,卢浮宫里要是没有玻璃把《蒙娜·丽莎》与参观者隔开,我们几乎就能触摸到它,由此我们与其历史的距离被拉近了,但同时我们经验到了作为鸿沟的历史传统,即作为艺术品温床和意义源泉的历史传统。
在奥若蒂克的艺术品中,感性成分与超感性成分、物质能指与精神所指,胶着不可分,注意到这点很重要。同样,伽达默尔在《美的现实性》中顺带对本雅明这篇随笔作过简短却富有启发性的讨论。正如他书中所言,奥若蒂克的艺术品可视作一种象征。[8]解构一件奥若蒂克式的作品,也摧毁了其历史的远距离在场。因此,解构一件奥若蒂克式的艺术品,不管它是否跟宗教内涵有关,都逐渐被理解为一种亵渎行为。[9]
对本雅明而言,要经验到光韵,并不限于艺术品之类的历史对象,注意到这点也同样重要。本雅明也把光韵概念用于自然对象。我们在地平线上注视山脉,或一根树枝向我们投下阴影,我们同样经验到了某种光韵,这时候:光韵即自然史,那座山脉或那根树枝的自然史。[10]我们同样可以想一想,我们在观看或触摸(例如)一块恐龙化石时,我们所经验的历史感。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基本论断之一是,在机械复制时代,通过印刷、照相和电影,我们经验到光韵的迅速消散:
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这是一个有明显特征的过程,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艺术领域之外、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各自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被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11]
有人可能会说,图像的机械复制,在时空上把事物拉得更近。为了看《蒙娜·丽莎》,我不必再去巴黎——就算是在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去趟巴黎也得花上数小时,我可以在艺术杂志或——今天甚至更为方便——在我的手机上(跟互联网联通)直接随时查看一幅复制品。奥若蒂克式的对象,其独一无二性和永恒性正被“暂时性和可复制性”取代。[12]

图二:“我的艺术空间”便于艺术爱好者“搜集”文化复制品
在刚才所举例子——《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中,该复制品仍然参照了艺术品原作,该复制品(只)是原作的一个副本。然而,要紧的是,本雅明在论证中声称,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膜拜价值随着光韵一起逐渐消失了。利用照相和电影之类机械复制媒体,原本与副本整个区分失去了意义。当然,有人会试图保留这种膜拜价值,例如照片只冲洗限量版或让摄影师签个名在上面,但诸如此类自欺欺人的做法,实际上只是在确认作品身上光韵的消失。膜拜价值让位于展示价值。例如,Andy Warhol复制《蒙娜·丽莎》,尽管仍然参照了达·芬奇原画,但其价值在这件复制品本身,并跟可复制性密切相关。

图三:Andy Warhol的《蒙娜·丽莎》,1978
传统意义上,事物先被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复制,而在机械复制时代,复制就是产品制造的直接目的。“复制艺术品越来越成了着眼于对可复制性艺术品的复制。”[13]
在本雅明看来,展示价值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在机械复制起作用的一切文化领域都成了支配原则。在其随笔中,他特别聚焦于政治。[14]在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机之类的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的成功尤其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传媒受众的欢迎,即依赖于他们的展示价值。
本雅明的这篇随笔意涵忧郁。光韵在早期照片中,随人类脸部飞逝的表情最后一次散发出来,他谈及于此,不光在为这些早期照片“无与伦比的美”和“忧郁”[15]而哀悼,他也在为在机械复制时代我们经验到人类本身失去光韵而哀悼。然而,与此同时——这显示了本雅明这篇随笔的根本含糊性——他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即艺术品的技术复制将——反对政治的法西斯审美化——使进步的艺术家把艺术政治化,让大众革命化。机械复制的发展既不能简单地欢呼为文化进步,也不能简单地宣判为文化衰落。机械复制在以新的方式揭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和危险。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数字化操控时,我们要记着媒体发展的这种根本含糊性。
3.数据库本体论
在媒体研究中,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被征引的文本,无出其右者。[16]无人惊讶于此,似乎只是因为他先知式的洞见,跟数字化重组时代能搭上边。然而,我们都知道,尽管计算机还只是一种机械机器,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数字化复制等同于机械复制(因此我偏爱“数字化重组”这个短语)。尽管计算机可以模拟各种经典的机械机器和媒体,如打字机、录音机或一个用于照片和电影图像的剪辑和演示的设备,但它有这一特殊媒体专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能证明,声称计算机代表了媒体发展的新阶段是合理的。
作为艺术媒体的计算机,我将对其基本操作规则作一简要概括。鉴于计算机操作的灵活性,此举也许看似野心过大。当作媒体来理解的计算机,不是一种媒体而是多种媒体。我刚举的这个例子(即计算机能模拟多种机械设备)表明,艺术家借助计算机,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制作、存储、演示和分类所谓“新媒体艺术”。例如,作为一种制作方式,计算机能让艺术家创作数字化图像和声音,建立交互式装置,设计多媒体站点,或为自我演进的艺术形式编程。然而,我想坚持是,在基础层次,凡媒体艺术品都分享了一些基本的特征。尽管各具体媒体艺术品可能在很多不同方面相互有别,并因此显示出家族相似而非单一本质,但在基础层面,它们都分享了持久存储的四个基本操作,这四个操作几乎是所有计算机软件都包含必备的部分。这种ABCD处理模式由添加、浏览、变更和粉碎四种操作构成。17这四种操作一起构成我们所谓数据库本体论的动态元件。
在计算时,数据库可以定义为一种结构化记录或数据的集合,这一集合被存储在一台计算机中,一个程序即可向它咨询,以回应各种查询。18这四种基本操作对应于结构化查询语言(SQL)的<插入><选择><更新><删除>命令。在这四种操作的帮助下,原则上,各种记录可以创造一切可能的组合。数据库本体论是动态的,因为元件数量在不断组合、去组合和再组合。
实际上,不是所有数据库都这样灵活。传统的纸质数据库倒是相当不灵活。一种经典的即“平面的”数据库由大量卡片组成,卡片上有数量有限且固定的信息组,以便输入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之类的信息。尽管不存在值得探究的结构性关系,但把数据库区别分类——例如,为了投寄按国家分组记录——还是可能的,不过那样会耗费大量时间。尽管这样一个平面数据库的电子版按不同范畴尽可能加速了分类,但它仍然非常缺少灵活性。
从1950年代开始,新的数据库不断得以发展,例如50年代出现分等级模型,60年代出现网络模型,70年代出现关系模型。最后一种模型以谓词逻辑和集合论为基础19,包括了若干表格,每个表格都跟“平面”数据库模型中的表格相似。关系数据库是多维的,因此其复杂性不能在一个平面上呈现,甚至不能在一个三维模型中呈现。关系模型的效力之一是,原则上,只要任何值出现在两个不同记录(它们属于同一表格或不同表格)中,都暗示着这两种记录存在关联。关系模型非常灵活,因为他们让用户有能力应对数据库设计者没预料到的查询。从1980年代开始,面向对象的编程也用于创造一种新的数据库模型,即所谓对象数据库系统。关系模型有时与面向对象的模型范式结合,然而它仍是支配性模型。
这些数据库模型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视作以特殊的方式再现、构造和扩展这个世界的一种界面。在考察数据库模型的发展时,我们注意到一种趋势:灵活性越来越大,应用范围的急剧增长。数据应用事实上超出了整个计算机软件领域,从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和WIKI延伸到工业生产和生物技术(例如基因工程)中的大批量定制。而且,各种数据库本体论带来的冲击不限于计算世界。
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发现,在只有锤子的人眼里,一切事物似乎都像成了钉子。世界范围内有超过500亿台处理器在工作,在计算机已经成为支配性技术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数据库。数据库本体论不仅塑造我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同时我们也日益从数据库的视角来塑造世界和自身。本雅明在那篇随笔中论证了,在机械复制时代,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机械复制的对象。讨论有时所谓的世界观机械化,他的随笔很有创见。在数字化重组时代,一切事物(自然和文化同样)都成了数据库操控的对象。这对我们的世界观的冲击意义深远。
我们以基因工程为例。地球上的生命,首先不再被看作一个高等种群,是偶然地、一步一步地演化而来的(在经典达尔文主义中是如此),生命更应该看作一个数据库即一个基因库,这个数据库包括数量无限的虚拟有机体和生命形式,它们可以随意变成实物。尽管还没有在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或在科幻电影《机械战警》中那么引人入胜,但由数据库技术创造的生命形式,正日益成为我们世界的居民。比如,为什么不能创造一只背上长有人耳的老鼠或设计一只荧光兔来瞧瞧呢?


图四:长人耳的老鼠,马塞诸萨大学 图五:Eduard Kac,白化荧光兔,2000
医学中心,1995
跟《侏罗纪公园》或《机械战警》不同,这两个例子不纯粹是数字图像化的产物。老鼠背上被植入人造人耳是一项医学试验的结果,这项试验由Charles Vacanti于1995年在马塞诸萨大学医学中心完成。而这只fluo兔则由巴西艺术家Eduard Kac“创造”,他委托一家法国实验室,而该实验室的科学家把一只太平洋海母身上的绿色荧光蛋白(GFP)注射到一只白化变种的兔子的卵中,制作了一只经“基因改造”的小兔子。
Vacanti和Kac的试验引起伦理争论的高涨。而且,针对Kac案例,人们也提这样一个问题:这件“作品”能称作一件艺术品么?在此意义上,这只兔子与约90年前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引发的问题类似。比如说,杜尚那时的作品《L.H.O.O.Q.》,一件便宜的、明信片大小的《蒙娜·丽莎》复制品,杜尚在上面添了胡髭。

图六:马塞尔·杜尚,《L.H.O.O.Q.》,1919
杜尚的《L.H.O.O.Q.》和Kac的荧光兔引发了它们是不是艺术品这一问题,而实际真相是,他们都运用了一种新的、看似非艺术的制作媒介作为艺术制作的手段,是在质问艺术与非艺术对象之间的区别。然而,尽管这些背景知识也许能说明何以会出现这一美学问题,但光说明问题何以出现,还不能解答问题本身。本雅明那篇随笔提供了一种答案,而我们需要再回到那一答案。
4.数据库美学
在《机械复制的艺术时代》中,本雅明认为,一个特殊对象是否该视作艺术品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定论。一个对象,一开始曾是件巫术法器,后来也可能逐渐被看作艺术品。本雅明暗示,同样,“绝对强调其展示价值,艺术品成了具有全新功能的创造物。我们现在意识到了这种创造物的艺术功能,以后人们又在某种程度上把它视作一种退化了的功能”。20
在机械复制时代,要区分复制品的艺术和非艺术功能已变得很困难,因而,比如要区分政治的审美化和艺术的政治化(它在本雅明那篇随笔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很困难。到了数字化重组时代,这种区分就完全模糊了。我将向你们展示荷兰计算机艺术家和影像专家Geert Mul新近的数据库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受在鹿特丹的荷兰摄影博物馆的委托,Mul建造了这个交互装置W4(Who,What,When,Where)。21这个装置由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80.000幅来自博物馆数字化档案库的照片)和当过滤器用的四个选项(post)组成。在Who,What,When,Where功能的帮助下,用户可以浏览博物馆内所有数字化藏品。例如,人们可以查看1936年在德国制作的关于花的照片。或所有制作于1900至1920年间关于《蒙娜·丽莎》照片。这个装置可视作一个设计来让参观者演示博物馆藏品的界面。该博物馆的每位参观者都变成了可自己布展的馆长。但同时,它是一件令人震撼的交互式艺术品,这件艺术品将参观者变成影像专家,是他们让照片成了有旋律的曲子。

图七:Geert Mul,W4(Who,What,When,Where),2007
这个装置的操控价值,既让它成了人-机界面设计绝佳的例子,又让它成了一件自主的艺术品。在数字化重组时代,一个对象的价值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是可操控的。22对于当代学者来说,本雅明全集的数字版比起传统的纸质版更有价值得多,因为它让学者(例如)在瞬间选出所有出现“aura”的页码。一件作品的审美品质强烈依赖于程序和用户界面的精确和简练。“数据库‘美’的‘观念’,不存在于观者解释一种静态形式的过程中,而存在于用户与数据库的信息组或结构互动而如何改变数据库的动态操控过程中”。23数据库播放本身一变成目标,数据库就成了一件自主的艺术品。W4表明,一个数据库可以同时是用户应用界面设计的活例子和自主的艺术品。
一个数据库可重组的次数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在数字化重组时代的艺术品,让光韵回归了。特别是在用户能改变数据库的内容并且在数据库中加入新的成分时,每一次查询都是一次独特的重组。结果,被数字化重组的艺术品重新获得某种仪式性维度。它再次成为感性成分和超感性成分之间的界面。然而,这次超感性成分不再存在于作品的历史中,而存在于它的虚拟性中,即存在于各种可能重组的无形总体性中。在文化领域,例如我们可以想到“百万蒙娜·丽莎”之类的站点,在那里,访问者正被邀请去创造和讨论自己个性版的《蒙娜·丽莎》。24我们在这些版本中见证了“光韵的回归”。然而它是一次变了味的回归: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一系列“原作的、光韵的副本”。25光韵回归变味了,因为数字化操控的对象甚至比机械复制品存在时间还短。因为其可操控性,数字化对象看起来天生就不稳定,像是艺术表演过程而不是成品。26

图八:“百万蒙娜·丽莎”(www.megamonalisa.com/)集合了
成千上万用户提交的蒙娜·丽莎艺术品
正如已提到的,数据库本体论不限于文化领域,也可以应用于自然。在这两个领域,数据库本体论显示出一种后-历史的特征。在数字化重组时代,恐龙不再是完全灭绝的物种,它们也已变成将来的可能性。27结果又将是一系列“光韵副本”。毕竟,当它们将在彻底变化的环境出现时,它们不可避免会变成另外的物种。
根据其用途,数字化重组的对象,比如Kac的荧光兔可能算是艺术品。然而,跟本雅明一样,我们想知道这样的作品是否能作为政治的艺术品起作用。数字化重组作为一种制作手段与机械复制品一样充满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正日益变得依赖于操控信息的能力。本雅明这篇随笔中最有预言性的断言之一是,在机械复制的时代,政治领袖的成功日益依赖于其展示价值。不过,在西方世界,原先当过电影演员里根可能算是最后一位仍能主要依靠其展示价值的总统了。在数字化重组时代,政治家们正越来越依赖其操控价值。我们不仅该想到他们可能故意操控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选举,也该想到他们可能从事非-犯罪的日常数据重组,为的是创造、控制和评价金融、经济和社会政策。
然而,对一件要具有政治性的艺术品而言,光被数字化重组还不够。数字化重组艺术品有别于数字化重组对象,因为它们还有反思的品质。一件艺术品把接受者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一媒介本身从而挑战他们。艺术品是自我反思的媒介。它们政治性的,不是因为它们再现政治,而是因为它们让我们意识到再现过程的政治性。同样,它们是政治性的,不是因为它们操控政治,而是因为反思操控的政治性。只有直到荧光兔让我们反思我们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媒体的工作时,它才能被称作政治艺术。28
一件能引起观者政治反思的作品是Geert Mul的《每日匹配》(2006),该作品是一系列名为“分离再现”的数据库作品的一个部分。在《每日匹配》案例中,“一台计算机在随机区间搜集来自大约三十个国际卫星电视频道的图像。在晚上,图象识别软件分析这些被记录下的图像。它比较电视新闻与电视广告。这个软件把每幅图像都跟其他每幅储存在电脑中的图像作比较,同时在每幅图像上较检5000个指定的专门点。在十亿次比较后,计算机生成一个列表。共享最多特征的图像成对地出现在清单的顶部。接着艺术家从成百上千的成对图像(根据计算机,它们作了很好的视觉匹配)中选取数对图像。每日email群发,订户收到这份精选品:每日匹配。”29
图九:Geert Mul,《每日匹配》,2006
把电视新闻跟电视广告作比较,每日的各种匹配再现了西方世界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这个层面上,它是对政治的一种再现和操控。然而,接受者也逐渐意识到了再现和操控的政治性。“计算机不‘理解’这些图像,它只是运用象素统计而已。对人眼来说,视觉相似性跟象素统计比是某种别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看’离不开赋予我们所看事物以‘意义’的解释。特别是当相似的图像看起来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时,这点就尤为明显。由计算机发现同时由艺术家选择的‘匹配’引起了诗意的、诙谐的、美的或厌恶的感觉。”30但我们逐渐意识到,就算是我们所发明的技术,其运作方式也有不可思议之处。同样,我们甚至开始反思这些新媒体非人的、甚至可能是野蛮的特征,或反思它有可能逐渐超出我们添加、浏览、变更和粉碎等技能的控制。我们也可能会成为数字化操控的最终对象。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担心机械复制品会让人类疏远。尽管本雅明意识到:我们也许有可能是在生命演进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后继者并由此让自身多余的第一个物种,不过他诸多担心或许不久就会变成怀旧的对象。
[1] 我们必须意识到,“媒体”概念包含诸多不同范畴,我们按这些范畴定义媒体,并把一些媒体跟其他媒体区分开。就算我们只局限于谈论所谓的“新媒体”(或“计算机媒体”),“媒体”一词也可能指多种不同的东西,比如物质载体(如磁带,CD,软盘,硬盘,U盘);初级编辑技术(如文字处理软件,网络集中编址存储器,绘图程序,合成器),存储复制技术(如CD烧录,复制数码文件),象征-质料形式(如直播流,站点,邮件列表),分流设备(如广播,Web服务器,网络)等。如果下文用到“媒体”一词,读者需要意识到,文中分析需要再对这些不同方面的媒介物作更进一步细化的考察。
[2]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媒体决定论。“技术并不决定社会:技术是社会的体现。但社会也不决定技术革新:社会运用技术革新。”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5. 换言之,在跟其他文化领域(比如科学、经济和政治)持续辩证地交互作用中,媒体得到发展,所以媒体不能从人类的行为和决定中抽取出来。为此,反思作为我们生活臂膀的媒体,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
[3] 从机械化到信息化转型的细节分析,参见Jos de Mul,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he Worldview."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 (1999): 604-29.
[4] Walter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2. Frankfurt a/M, 1974; 本文引用的是H. Zohn的英译本: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我用的是该译本的在线版,链接地址为: http://pages.emerson.edu/Courses/spring00/ in123/workofart/benjamin.htm.
[5] “Das Kunstwerk”. Op cit. ——原注。 见中译本(王才勇所译《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52、53页。因为Jos de Mul先生引用的是在线英文版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以引文出处无法标明具体页码。——中译者注
[6] “Das Kunstwerk”. Op cit. 见中译本第58页。
[7] “Das Kunstwerk”. Op cit. 见中译本第149页。
[8] Hans Georg Gadamer. 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86. 33.
[9] The relevance of Beauty and Other Essays. Op cit. 33-4. 关于“亵渎艺术”也可参见Jos de Mul. "Résonances de la mort de Dieu, Après les fins de l'art." Figures de l'Art. Revue d'Études Esthétiques. No X: L'esthétique, aujourd'hui? Ed. Bernard Lafarque (2005): 265-77.
[10] “Das Kunstwerk”. Op cit.
[11] “Das Kunstwerk”. Op cit. 见中译本第53页。
[12] “Das Kunstwerk”. Op cit.
[13] “Das Kunstwerk”. Op cit. 见中译本第120页。
[14] “Das Kunstwerk”. Op cit.
[15] “Das Kunstwerk”. Op cit.
[16] 一些出版物的标题甚至参考了本雅明这篇随笔。参见: David Harvey.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Reproductio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c Blackwell, 1989. 346-50; Douglas Davis.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 An Evolving Thesis." Leonardo 28.5 (1995): 381-86. Douglas H. Thomso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Re)Production". 1998. Romanticism on the web. (May 1998). http://users.ox.ac.uk/~scat0385/work.html; Hans Ulich Gumbrecht and Michael Marrinan, eds. Mapping Benjamin : The Work of Art in the Digital Age.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3.
17 这四种基本操作也用CRUD(创建、读取、更新、删除)和ACID(添加、变更、查询、删除)的首字母缩写来表示。
18 实际上,“数据库”(database)这个词可以指三种不同的东西:1)正在被存储的数据;2)数据存储和连接的方式,即数据库模型;以及3)用于存储和操控数据的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在上下文中,我主要指的是数据库模型。
19 E.F. Codd. "A Relational Model of Data for Large Shared Data Bank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3 6 (1970): 377-87.
20 Benjamin, Walter. “Das Kunstwerk”. Op cit. 见中译本第64页,引文有改动。
21 见www.geertmul.nl.
22 William Mitchell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较点。Mitchell, William J. The Reconfigured Eye: Visual Truth in the Post-Photographic Era.Cambridge: MIT, 1994. 52. Daniel,Sharon. "Collaborative Systems: Evolving Databases and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 Artificial Life Models of Agency in on-Line Interactive Art." AI & Society. The Journal of Human-Centred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4.2. Database Aesthetics: Issues of Organization and Category in Online Art (2000): 196-213.
23 Daniel,Sharon. "Collaborative Systems: Evolving Databases and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 Artificial Life Models of Agency in on-Line Interactive Art." AI & Society. The Journal of Human-Centred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4.2. Database Aesthetics: Issues of Organization and Category in Online Art (2000): 196-213.
24 回过头来想,从数据本体论的观点来看,专属于奥若蒂克传统的艺术品就可以不同面貌重现。那些由蒙德里安和斯特拉制作出来的艺术品,或在单个作品内利用元素重组的艺术品(如Steve Reich的简约音乐),就是可这样重新看待的例子。
25 Cf. Douglas Davis.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 An Evolving Thesis." Leonardo 28.5 (1995): 381-86.
26Eric Bolleet. al Book for the Unstable Media. Den Bosch: V2, 1992.
27 在此意义上,数据库本体论是虚拟的现实(被看作无限量的可能重组)与实现了的虚拟(被实际实现出来的重组)的结合。
28 尽管艺术家的意图不是决定性的,但就Kac案例来说,其目标无疑是政治性的。“我的作品不是为了让科学形象化。它并不打算复制从科学向媒体、向公众传播的信息。它试图介入、改变、批评、指出、反思和修正那样的信息。”引自Ulli Allmendinger. "One Small Hop for Alba, One Large Hop for Mankind." NY Arts Magazine 2001.
29 描述来自: www.geertmul.nl/Geert_Mul/MATCH-OF-THE-DAY.html
30 Geert Mul. Op.cit




 Vanaf de derde druk verschijnt
Vanaf de derde druk verschijnt